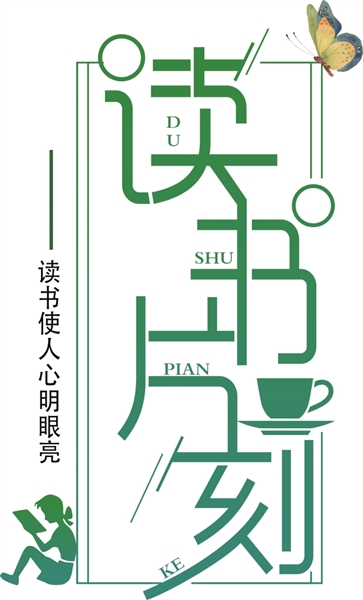分享者:郑凌红
看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柳暗,是《我与地坛》沿袭的悲情余温;花明,则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豁达和释然。两者单独成秀不难,相得益彰就难了。
古今中外,真正优秀的写作在于打动人心,可人心总是游移不定。窃以为,打动人心有一密钥:生命体验(即人生感悟)。显然,《病隙碎笔》属于这一类。史铁生的青春是“破碎”的,命运对他并不温柔,反而打上了“残疾人”的标签,更为不幸的是,从身体层面还被施以“晴天霹雳”——确诊尿毒症后终日以透析延续生命。
跳出肉体的痛苦,对常人来说已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可是,他努力逃出自卑心理,以清醒的目光拥抱自我的“小爱”与普适性的“大爱”。他知晓爱的平等性,他说“爱不是求助于他者的施予,是求助于他者的参加”。他也以直面而坦率的热情把自己对于爱和性的渴望跃然纸上,只是在两者之间,他冷静地割裂看待,未曾倾斜于一方。
再来说“完整”。他的完整,体现在对社会群体的“大爱”。从《三国演义》中赵子龙斩上将首级而喝彩时,那些被斩首而不曾留下姓名的将士们,他们有亲人吗?有自己的生活吗?提问之余,深沉的共情令人动容。
张路黎在《史铁生哲思文体研究》中如此评价:“在儒道互补为文化主流的中国文明里,忏悔意识是一个外来的异质性因素……出现了一批剖析灵魂,直指内心的文学。”作为主流的思想框架,回顾与忏悔贯穿了史铁生作品的全貌,只是作为“超前性”的彰显,在不经意之处触动了你的神经,我相信,读者在书中可以读到中国人的风骨。
史铁生“上山下乡”的经历,也许很多读者都未曾经历。可是,对于生命终点的思考,对于生态的前瞻性呼吁,字里行间的急迫,很明显地呈现出作家的格局和时代胸襟。这样的“完整”,是对社会的大爱。这心系苍生、悲天悯人的“大爱”,初读是一种感受,再读又是一种感受。
文学和人一样,都有两面性。一面宁静,一面热烈。优秀的作家,文字里可以看得到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更可见起伏中的宁静。破碎,是另一种完整。破碎,也成就了完整。《病隙碎笔》里提供了宏大而简约的“人间道”,那就是破碎的青春不因残疾而失去光彩,不破碎的爱充盈着真实而火热的人间。就像有人说的那样,这样的状态和斗志跟年轻时的杜甫一样,是凤凰涅槃,心高万仞,壮志凌云。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引用希腊哲人的话“万物各有二柄”,好比阴阳两极,而人会抓住其中一个把柄来做比喻,抓哪一头取决于人想说什么。
想起鲁米的一首诗,可作结尾:我的眼睛就像太阳,做出许诺;许诺着生命会拥抱每个晨朝。活生生的心给予着我们,恰如那光明天界的照耀,心与天界一同,以极大的温柔,爱抚着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