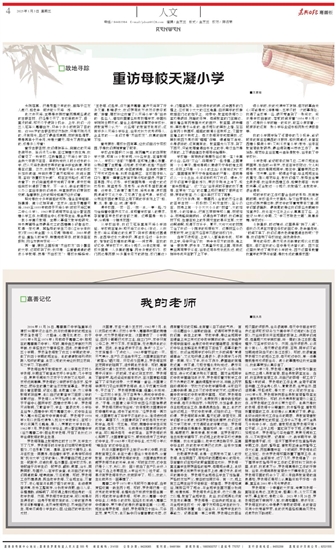■王家俊
光阴荏苒。已是耄耋之年的我,前阵子应友人邀约,和老伴一起去故乡天凝一游。
此次去天凝,主要是去蒋村看两棵闻名遐迩的古银杏树。已经是冬天了,本该早就去了,但一直没时间,那天终于逮到个机会。上午,我们一行三人驱车从嘉善出发,只半个多小时就到了目的地。近900岁的古银杏树依然挺拔,只是天阴沉沉的,没有阳光,且过了最佳观赏期,树叶有些凋零,要是再早十天半月,并是大晴天,阳光下满树金黄的,该是多么好看!
看好古银杏树,我们调转车头,向南边的天凝老街开去。车行没几分钟,在红旗塘大桥北堍,我们看见了一所学校,红色墙面上“天凝小学”四个金色大字赫然在目。早就听说我儿时念过书的小学,已从天凝老街倪家弄底的庵浜移址新建,原来是在这里。忽然,我想起几年前天凝小学的杨校长加我微信,并向我要了简历和照片,我问派甚用,答曰“布置校友长廊”。现在正好路过,何不进去看下?我们向值班保安说明了来意,保安打电话向校长通报了情况。不一会儿,新任的周校长从办公室出来接我们进去,并直接把我们带到校史廊,指着展板上我的照片和简历让我们看。
照片是我十多年前拍的那张,端坐在电脑前,挺精神。简介这样写道:“王家俊,出生于嘉善天凝,1949至1955年就读于天凝小学(时称天凝区第二中心小学)。1963年平湖师范毕业后分配在西塘小学工作,长期担任中心校教导主任,是全县第一批小学高级教师。主要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并负责辅导全市最早成立的西塘镇小记者活动,取得一定成绩。其指导的学生习作《江爷爷来我家》获1992年全国‘少儿见闻’特等奖。2003年退休后,重拾儿时爱好,钟情阅读写作,时有作品在报刊、网络发表并获奖……”
再一看,展板上面标有“杰出校友”四个醒目的大字,这可吓到了我: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退休小学教师,岂是“杰出校友”?周校长解释说:“王老师,这些年,你为宣传嘉善、宣传天凝写了好多文章,影响很大,我们想用此方法对你表示感谢。”接着,周校长让我看了从天凝小学“走”出去的一些名人,诸如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顾功叙;曾任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校长、被教育界公认为“一代名师”的教育家赵宪初;还有许多从天凝小学毕业、后来成长为优秀领导人、企业家的……他们才是“杰出校友”,我真的自愧不如。
看完展板,周校长因有事,让我们自行参观校园,于是我们便随意看了起来。
学校占地面积约30亩,有两幢气派的四层教学大楼,现有14个教学班,559名学生,在编教师39人。学校以“古韵”为基调,在环境上精心布置,分别设置了主题墙、行知廊、校史廊(包括“杰出校友”)、红旗塘文化廊、中医廊棚等。在连廊处摆放了开放式图书角、科技作品展区。在校园绿地入口处,置有一尊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塑像,开辟了百果园、开心农场。学校南面则是一片偌大的运动场地,有篮球场、足球场、彩色环形塑胶跑道等。近年来,又新建了清风林、凝秀池等,使校园既浸润于文化之中,又充满了生活气息。学校还分别在校园的景观石上用不同的字体刻上了“和、勤、礼、孝、善、俭、诚、健”等字。
漫步校园,一花一石,一林一池,一亭一路,处处诠释着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着学校育人的要求,孕育着百年老校的古韵之美。这哪里是一所小学,分明是一个锦绣花园!
从学校出来,我们又驱车直奔天凝小学旧址。学校就在庵浜(现天凝文化中心)东边。从我老家(凝溪河南边的北廊下)到学校得越过圆通桥,往西穿过北大街中段,再往北经过一条长长的、窄窄的石板铺地的弄堂——倪家弄。在我的记忆中,原学校不大,就6个班级,10来位教师。学校外面是一人多高的围墙、两米多宽的校门。校门两边是两根30多厘米见方的砖柱,校门高近3米,门楣呈弧形。在我读书的时候,这半圆形的门楣上,应该有个大大的红五角星,白底黑字的校牌就挂在门边的柱子上。印象中,教室和老师办公室均是破旧、阴暗的平房。每间教室的门在南边,南北墙各有两扇推关式的窗户。教室里,砖块铺地,黑板是木头做的,油漆斑驳的黑板上端,左右各有两个铁圆环,粗粗的麻绳系在铁环上,又固定在墙上的大铁钉上。每次老师写字或擦黑板,这黑板就因为晃动而“哐哐”作响。课桌椅不消说,也是很旧的,还有高有低。教室里光线不足,到了下雨天,只能勉强看得出书本上的字,电灯当然是没有的,上下课由值日老师用手摇铜铃。
学校唯一有特色的是操场后边有一座7米高的小山,名曰“文山”,四周种了一些绿植,上面建有一个小亭子,据说是明代建造天宁寺时堆土而成,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土丘(也有说这叫“坟山”,里面埋有原天宁寺庙和尚的尸骨)。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土丘,也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课余,女孩子们在亭子里做游戏,男孩子则冲上冲下,玩“官兵捉强盗”。这“文山”后来何时平掉的我不清楚,在原先“文山”的位置上现已建起了居民住宅楼,原来的教室、办公室也早已不见了踪影。
校门外东侧,有一棵需两人合抱的历经沧桑的百年古树——枫杨树(又叫元宝树),至今仍在。树身上有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树瘤”,大的如足球,小的如拳头,已有三层楼房那么高,树冠如伞,树身略向南倾斜。记得当年下课时,我们常在树下玩,捡掉在地上的形同元宝的果实互掷,大家逃啊追啊,玩得不亦乐乎。夏天,大片大片的树荫又给了我们一个荫凉的玩耍地方。这棵树至今仍枝繁叶茂,屹立在历经百年风雨的旧校门外。
当年不像现在,上学人人都背新书包。那年我上学,母亲只给了我一块半米见方的旧布,角上缝一根布带,把书本、文具叠好放在上面,用布包裹后再用带子系住,后来还用牛皮纸包扎过,就这样将书包夹在腋下上下学。
读小学时,我的成绩并不怎样,但对时事尚关心(可能是受父亲影响),五年级时一次时事测验,我得了全校第一名,破天荒拿到了一张奖状。奖状是学校自制的,落款时间写着“1954年5月17日”,这是我小学时唯一的奖状,故至今保存着,一起保存的还有一张小学毕业证书和两张成绩报告单。
我的小学同学除了邻居中的几个玩伴,能记起来的有住在镇西的沈根林,和我同桌过,他曾在西塘小桐街小学(又叫毛家庵小学)教书,后来在教育局做教研员,最后调到嘉兴市去工作了。焦延龄,师范毕业后在嘉兴油车港教书,后来做了中学校长。
小学老师,能记起来这样几位:二年级班主任顾国英,她当时40来岁,家住在学校附近,女儿叫顾先英,和我是同班同学;梅奕中、董善英两位老师是一对夫妻,后来一起调往干窑;毕业班班主任包雪龙,刚从师范毕业,教我们语文;教导主任黄士昆老师,我后来去西塘工作,和黄老师在一所学校共事,还合教过一个班级,我教语文,他教数学,很合得来。
那时学校的工作均配合当时的形势,抗美援朝时期,学校组织大家捐钱,除交出零用钱外,还让我们拣废铜烂铁,把家中的牙膏壳带来交掉,同学们都很踊跃。最有趣的是让我们报名去朝鲜参加宣传队,我也在大红纸上认认真真签了名。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又“学习苏联老大哥”,跳集体舞,穿花衬衫……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这里虽早“换了人间”,但我仍沉浸在对昔日母校的回忆中,老伴催促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还得去老街看圆通古桥呢!”于是,我们告别了母校旧址,向老街走去。
原先的母校,虽然无法与新建的现代化校园相比,但它在我的心目中是无法替代的。因为在这里我度过了美好的小学时光,因为这里承载着我童年的梦想与希望,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