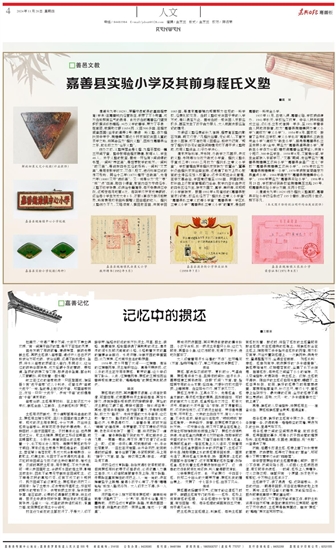■三篰草
杜甫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是天下百姓的夙愿。
祖先发明了用砖砌墙,建造房屋。制砖先要制土坯,再把土坯装入窑墩里,通过炉火日日夜夜地煅烧方可成砖。煅烧后期,还得不断地担水、登顶,将水从窑墩的顶部注入窑内,形同淬火,让烧红的砖块华丽转身,成为坚硬十足的青砖。要知道,登顶的砖梯又窄又陡,即使徒手登高,都会叫人双腿颤抖,何况挑着一担水哩!
屹立在江边的窑墩就像一只巨型面包,难怪吾乡有“包子窑墩”这么个叫法。还曾流传“窑廊大包子”一说,指的是上世纪的干窑。那里窑墩林立,犹如一只只“大包子”。传说“干窑”的称谓是由“千窑”演变来的。
窑墩烧砖,土坯是原材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制坯全由人工制作。土法制坯叫作“掼坯”。
取土
土坯用泥巴制成。家乡遍野都是乌油油的泥土,掼坯用土随处可取,且以水田里的黏土最为上乘。现成的泥土用来掼坯,十分方便。然后将土坯卖给窑墩头,就有花花绿绿的钞票进账。私人种田时,从自家田里取土。农村集体化后,社员掼坯计工分。取土也随便,掼坯的工场设在哪里,就在哪里取土。小辰光,常看到田头的土墩一个连着一个,也不知派什么用场。等摆开掼坯的场子才明白,原来这些土墩是为掼坯储备的。田间取土,若在某个角落挖取,形成大坑会影响耕作。分散取土,均衡土地,水田才不会变得坑坑洼洼。趁农忙时将田间各处挖沟的土块收集起来,堆成土墩。农闲时再把土取来,用于掼坯,不失为良策。可一味从良田里取土,会破坏水田的黏土层,影响庄稼生长,因此不能毫无节制地在田间取土。这不单是农民的真知灼见,还有不成文的乡规民约。既然田间不能恣意取土,掼坯用的泥巴又从何而来?除了土墩外,还去荒地开垦取土,好在那时野外的荒地不少。去荒地把土挖来,除去树根杂草、细石碎砖,必要时还得撑起三脚架,将土过筛。若泥土中混杂树叶杂草,掼出来的泥坯里含有杂质,经窑火一烧,成品的砖块结构疏松、承重力差,故而掼坯的用土十分讲究。
村庄近处能挖的土都挖没了,于是大人们不辞辛劳,摇船去较远的地方找泥土,开垦,担土,装船。晚霞旖旎,船舱里装满了黑黝黝的泥土,清凌凌的河水托起沉甸甸的小船,小船载着发家致富的憧憬徐徐前行。水波织锦,绘制家园的幸福蓝图;欸乃声声,汇成美好生活的畅想曲。
1958年,家乡开掘了大河——红旗塘。绵延的红旗塘两岸,泥土堆积如山。真是天赐良机,这么多的泥土正好用来掼坯。勤劳致富,让乡亲们有了盼头。从此,红旗塘两岸,掼坯的工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噼噼啪啪”的掼坯声此起彼伏。
踏泥
掼坯用的泥巴,其质量要求很高,必须细软柔滑、可塑性强,这就需要将泥土捣碎搓细,再加水揉匀,像搅拌面粉般地把泥巴揉顺揉滑。原始的泥土颗粒又硬又粗,要揉成面团一样谈何容易?再说,若用手来搓揉,显然自不量力,于是就用脚踩,称之为“踏泥”。先将家里的大水牛牵来,让它助一臂之力。踏泥时还得不断往泥土里加水,边踏边泼,水要洒得均匀。人牵着牛绳,时时发出“噢噢”的催促声。牛蒙着眼,不紧不慢地迈开四蹄,老老实实地转了一圈又一圈,将泥巴踩了一遍又一遍。看牛蹄踩踏不到的地方,赶忙前去补上几脚。一脚高一脚低,弄不好,脚下打滑了还会摔上一跤。还有一件烦心事,那就是时间一长,牛会拉屎撒尿。一旦拉在泥堆里,会污染泥巴,故而就得时时留神。看牛后腿下蹲,牛屁股撅起,马上用“撩子”(方言,音,指一种农用工具)接住,一点都马虎不得。
泥巴经过反复踩踏,渐渐变得松软柔韧起来,但离掼坯用料的要求还差很远,必须依靠人力精工细作,大人们绾起裤腿管赤足上阵,用力踩踏。赤脚踩在富有弹性的泥巴上,人一耸一耸的,像在弹簧垫子上跳舞,看得小孩子心痒了,于是“嘻嘻哈哈”地加入踏泥行列。大人们求之不得,多一人就多一份力。
泥巴踏成什么样方可用来掼坯呢?简单地说就是“泥踏熟了”。一个“熟”字,用汗水浇灌,用力量铸就。泥巴经过反复翻转、踩踏,变得像面团一样柔滑,将踏熟的泥巴一层层垒高,堆成一个“碉堡”。
要说泥巴像面团,其实更像做粑粑的糯米粉团。小孩子贪玩,抓一把泥土来捏只小鸟,让它飞起来,再捏条小鱼,让它游起来,玩得不亦乐乎,连吃饭都忘了。
大人们看着用汗水浇灌的“杰作”,拉开嘴笑(方言,指咧开嘴笑)了,第二天就能放手掼坯了。
掼坯
掼坯,都选择农闲时节。夏秋时分,气温尚高。掼坯是件体力活,且持续时间长,出汗也多。需要搭建工棚来遮阳。四根“杈闯”(方言,音,指搭棚专用的尖头木棍)竖四角,六根长竹构成田子顶,上铺棚荐。当空阳光灼灼,棚下凉风习习。
掼坯工序繁多,工具也不少。先是坯盒。坯盒木制的,是泥坯成型的模具,且拆卸自如。那时砖的制式为七五砖,坯盒规格与之对应。取来大泥弓,钢制的大泥弓呈“马”字样,底下绷着钢丝弦,切泥快如利刃,还不被泥土粘住。劳作者身围肚兜,开弓取土。大块的土四四方方,有七八十斤重,双手托住底,搿牢后隑住肚皮,“哧吭哧吭”搬至坯凳旁,一块块码好。接着,按掼坯要求剖成小长方块。一切安排妥当,就叉开双腿坐在坯凳上,像骑士那样雄赳赳地披挂上阵了。掼坯动作娴熟快速,先往坯盒内侧撒点毛灰防粘连;旋即举起初步塑成的长方形泥块,不偏不倚地用力掼入坯盒;再提起坯盒的一端在坯凳上厾厾结实,紧接着用小泥弓沿坯盒表面将多余的泥巴箍下;土坯还不够光洁,随即用蘸上水的抹坯棍来回地抹,一面抹光洁了,再将坯盒反转身来,换一面再抹;土坯的两面都光洁如镜了,这才用薄薄的坯板垫着;拆除坯盒,坯板托着土坯像模像样地出炉了。这一连串的动作做起来比说还快,叫人看得眼花缭乱。
父亲是掼坯行家。他一天能掼约一千四百个坯。我那二十出头的大哥更厉害,掼坯比武的擂台赛上,一天掼了一千七百多个坯,出足了风头。
擒坯
掼坯需选择晴好天气,这样才能让湿坯及时晾干。晾晒土坯有专门的场地——坯场。坯场上筑有晾坯的坯裙,一条条坯裙长长窄窄、笔笔直直,有如田塍一般。每条坯裙的间距有四五尺宽,利于通风采光。
把土坯侧立在坯裙上,叫擒坯。每块土坯都有坯板托着。搬运时,将垫了坯板的土坯叠起来搬往坯裙,放在坯裙侧的坯凳上。用擒坯板合在土坯上,随即用双手手指夹住坯板的两端,用力松紧有度,然后放置到坯裙上。一次擒两块,侧身安放,叠得整整齐齐,垒得密密麻麻。一列坯也叫一埭坯。坯排列有序,就像摆好的“多米诺骨牌”。擒坯要骑缝放,这样错落有致,垒高了也不会倒塌。抽掉坯板,每块坯之间留下小小的缝隙。风儿见缝插针,吹拂到每一块土坯上。这样,土坯就干得快。刚出炉的土坯还怕阳光直射,曝晒下,土坯容易坼裂。故而,擒好的坯要及时用草荐遮盖。草荐用稻草编织,长约三尺,宽约七寸,盖坯埭上恰到好处。最关键的还有,垒好的坯埭不得有丝毫倾斜,否则,大风一吹,“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上演了。
再是,擒坯的人见缝插针,将掼坯用土一一准备妥当。掼坯和擒坯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晾坯
每条坯埭,擒好的土坯有十层之多。坯埭一条接着一条,仿佛就是一堵堵镂空的花墙,更像列队的士兵,显得气势不凡。
每条坯埭之间的空间颇像弄堂,故称作坯弄。坯弄里面故事多,那是小孩子捉迷藏的理想场所,在坯弄里奔跑,北面进、南面出,玩“失踪”,兴奋得丢了魂。
夜晚,怕露水打湿土坯,坯埭上盖了长长宽宽的草荐。夜色朦胧,坯弄成了隐秘的“草舍”,那可是乡下男女青年约会的“咖啡屋”。
辛辛苦苦掼出来的土坯需要精心呵护。若天公不作美,夜间突降小雨,人们担心土坯被雨淋湿,赶紧起来去遮坯。一时间,坯场上人声嘈杂,灯火忽隐忽现。谁都只有一个愿望:祈求老天爷帮帮忙,千万别让土坯泡汤了。
土坯晾干了,装了满满一船,运到窑墩头。多日的付出,一朝得来回报,笑容在古铜色的脸上绽放。再说,土坯不经窑火的锤炼,怎能坚如石头、担负起建筑高楼大厦的重任呢?
21世纪初,为了推行节能减排工作,保护土地资源与自然环境,新型的建筑材料应声而起,窑墩成了历史遗迹,土坯更是销声匿迹。唯独“掼坯”的“噼啪”声犹在耳际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