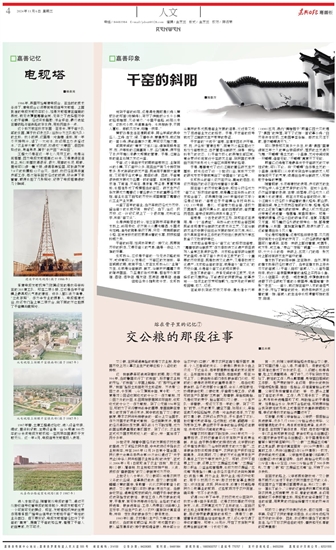■陆勤方
说到干窑的斜阳,还是得先提起清代诗人黄杞孙的那首《归棹诗》,写尽了傍晚时分水乡小镇的轻柔雅丽、风姿绰约:“十里干窑路,斜阳淡未收。依桥成小市,夹浦集渔舟。水共柳新绿,云同人暮愁。卸帆风亦缓,归橹一枝柔。”
黄杞孙是生活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邑中名人,工诗、古文、词,又善书法,兼精篆刻,就这样的一首小诗,便能品精妙之趣,更可见风雅之情。
咸同年间的“粤变”之乱以后,避难而躲身在苏、杭、沪等地的江南富有人家、名门高第,便开启了淞沪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营建。于是,江南各地的窑业也随之发达兴盛。
干窑,这个早自宋元时期就窑墩林立、业陶而兴的小镇,不仅窑户众多,而且出产有几十种花样繁多、形式新颖的砖瓦产品,既适用于高楼大堂建筑,又可用于各式亭台、榭阁修造。因此,干窑竟很快就发展成为名震一时的窑都。地域相近的洪家滩、下甸庙、天凝庄、清凉庵、界泾港、夏墓荡等地,也相继形成了规模相当的窑区。砖瓦生产逐渐发展成为嘉善这个著名粮仓之地的重要经济支柱,窑业也在不自知的历史长河里奠基了嘉善近代工业产业发展。
兴盛了百年的窑业,当然早就已经成为历史,留给窑乡的也就只有一种记忆。当下,给这一段历史、这一份记忆冠上了一个很优雅、动听的名字,叫做“窑文化”。
也是傍晚落日时分,站立在跨市河窑港的楠木桥上,斜阳未收,依然有淡淡霞光铺洒,水面波光如鳞,渔舟的踪影早已不再,只见一玻璃钢制的小船,在缓缓移动时打捞漂浮着的水草、树枝和塑料瓶之类。
干窑的斜阳,如何去写意这一种文化,既要有历史的积淀,又要见窑火的气息,确是一件让人为难的好事。
北环桥头,应该是干窑的一处无法忽略的地方,或许竟可以认定是这一方窑区的发祥地。早在明朝初期,就有干姓人家在北环桥头以“业陶”为生,也就是烧窑制砖、制瓦,烧制坛坛罐罐之类的陶质器皿。及至清初渐成市集,相继开办有茶馆、酒店、烟杂店、理发店、豆腐店、糖果店、油酱店和各类小摊贩数十家。北环桥头集市的形成既是窑业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了促进窑业发达的标志。于是,干家窑的称号就成了江南砖瓦生产繁荣的象征。
干家窑的“大包子”窑墩,在清末因淞沪开埠,苏、杭、沪各地“营建日繁”,而竟然泛滥至相近之地处处窑墩林立、日夜冒烟烧制砖瓦,倒是一种始料未及的状态。以干窑为核心的县境北部区域,竟会累计修筑有近千座砖瓦土窑,到民国初年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七大窑区共同繁荣的格局。
于是,嘉善竟成了近代江南的著名砖瓦生产基地。时光流过了近一个世纪以后,有地方文史的研究专家干脆就亮出了“中国窑乡”的名号。
北环桥头的窑火依然在燃烧,高耸的烟囱,也依然用自己的姿态在诉说着窑乡故事。
而在窑乡的历史故事当中,现如今已经成为“窑文化”标志性的窑墩,就是矗立在乌桥头的沈家和合窑了。依县博物馆2007年编印的文字介绍是这样的:“窑墩位于干窑镇治本村乌桥头132、133号前。清代。该窑墩为和合窑,结构为双圆筒形,呈两只馒头状,窑的四周砌砖,窑顶置两烟囱,窑旁设有砖阶供挑水者上下。”
窑墩是一个古老的砖瓦工场,到现在还在使用,是一个“活遗址”。乌桥头的沈家和合窑因其既能体现清末烧制砖瓦的技术与工艺,又在烧制砖瓦活动中展示出社会发展的样式与风貌,所以,作为具有百年手工作坊的历史性代表被列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沈家和合窑是如今“窑文化”的标志性窑墩,“嘉善京砖烧制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列入省第三批保护名录。沈家和合窑京砖烧制技艺的呈现,书写了窑乡传统手工技艺的又一个重要的历史项目,既是物质文化遗产,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沈家和合窑的存在,就是窑乡“窑文化”的历史价值,也是窑乡窑文化的现实展示。
生生不息的窑火,传承无间的手工技艺,无法释怀的风情民俗,不能遗忘的民歌民谣、故事传说……如泥土的芬芳那样飘飞,如岁月的天籁那般回响,悠久、辽远。
在能够找到的历史文字中,清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邑内“博雅君子”顾福仁因大风吹塌了“偶园”的房屋,写下了这样一首记事小诗:“白云来去本忘机,三载园亭客渐稀。昨夜北风狂不歇,居然蝴蝶满天飞。”
可以想象那风有多大多狂,吹得“偶园”里建造有三年之久的亭台楼阁倾圮,屋顶的土瓦满天飞舞。“天蝴蝶”是土瓦的一个品牌,瓦片中间印有一只蝴蝶,谐音无敌,“天蝴蝶”寓意天下无敌。
顾福仁这诗是不是最早关于干窑砖瓦的文学性记载,可以不论。将“天蝴蝶”当作是土瓦的一个品牌,倒是可以从中感受到当年烧制砖瓦人那种雄视天下的气度,读得出当年烧制砖瓦人那种敢于争锋的豪情。
随着钢筋、水泥等建材的使用,传统砖瓦的生产开始步入手工技艺保护的行列。在城乡各地,仍然留存着的老街、古巷、旧屋等,已经成为人们寄寓乡愁的建筑。就在沈家和合窑的附近,有一个江南水乡已经极少保留着的清代船坞,歇山顶,面阔四间,岸上为花岗石堆砌的驳岸、船埠,船坞的边上还有几幢残破的楼房。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近旁竟还逶迤着一堵围墙,弯曲而绵长。那是一堵青砖裸墙,已经泛白的砖缝泥浆,细腻、平整而又笔直。那几幢已经残破的楼房也一样,都是青砖裸墙,从地面一直挺直到墙顶,即使残破了,也还能看得出乌斗风火墙。
无论是那堵围墙,还是那些旧楼老屋,风风雨雨总有数十近百年的岁月了。从已经破损的墙脚里可以看得到,在每一块砖上都印着章,或圆形,或方形,或三角,“泰山”“定超”“明富”……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每一块砖上,五花八门的每一张瓦片上都印有砖瓦生产窑户的章。
楠木桥下的斜阳余晖,正在隐去。当然,原来的楠木桥早已经改建过了。当年在楠木桥上来去匆匆的窑廊人(干窑人自称“窑廊人”),从窑场里归来,就近从窑港里横停着的渔船上买两条小鱼,又从小店里买一包烟、一瓶老黄酒,步履稳健地走进眼下已经破败不堪的小巷里弄,嘴里喊着“老张”“老王”……窑乡,就这样在窑户人家的油烟气息之中,开始了黄昏的时光。就像每块砖瓦上印着的章一样,窑廊人的生活中也弥漫着那样的笃定、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