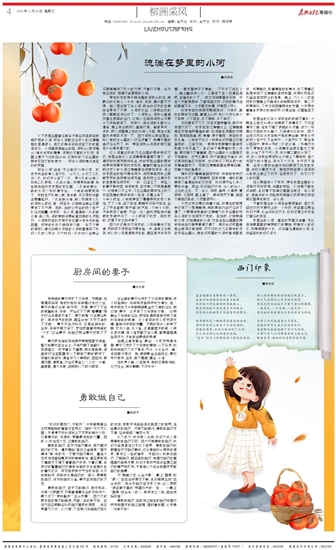■吴建昌
乡下老屋后面曾经有条没有名字且存在时间极短的小河,那条小河跟流经家乡的红旗塘相比显得很小,但它还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深处。小河里装满稻谷的船、河桥头(即河埠头)淘米洗菜的情景、河岸边笔直的水杉树、河面上偶尔飞过的白头翁,还有我的几位山里的同学见到它时的激动……那条小河时常流淌在我的梦里。
那条小河“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我老家所在的第七生产队一分为二,分成了二队与八队,我们家分在了八队。原小队的仓库公场归二队使用,八队的仓库公场要易地新建,地址就选在我家老屋的东北面。八队新的粮仓、新的水泥公场修建好后,一个新的问题就来了。那时生产队粜公粮、卖余粮、买农用物资都主要靠船只。八队的新仓库、新公场离老七队的河桥头很远,有一两百米,这样就给粜谷买肥带来了不方便。因此,当时分开后的两个生产队经过商量,决定挖一条小河,直通新八队的新仓库、新公场,河的宽和深要能通五吨的水泥船只。小河就挖在我家房子东北面十来米远的稻田里。那年的秋收冬种到来之前,一条不太宽的但可以通行五吨水泥船的小河就直通到了我们八队的公场边,它为我们八队秋收以后粜谷买肥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尽管它只是一条没有名字的、短得不能再短的小河。
原先我家的房子离浜里的河桥头较远,离最近的也有七八十米,淘米、洗菜、提水都不方便。自从屋后有了条小河,就给我们家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方便。小河挖成后,父亲就让我的两个哥哥在河边修了一个河桥头,河桥头直通家里灶披间的后门,这样从灶间到河桥头只要十几步路就到了。那年代,每条河的水都十分清澈,提上来后就可以直接饮用。稍微考究一点的,把从河里提上来的水倒入水缸,再往水缸里放点明矾沉淀一下。因为河桥头就在屋后,所以有时灶头里的火已经点着了,铁镬子里的油已经烧热了,叫一声在河桥头洗菜的赶紧回来炒也是来得及的。
这小河曾让我的几位山里的同学惊诧不已,说屋后有这么条河真是幸福得不得了。记得那时我师范即将毕业,我的那些山里的同学说想利用周末到我家玩玩,看看我曾给他们讲起过家乡的大河红旗塘是如何宽如何深、河上东来西往的船只是如何多、河两岸桑树地上郁郁葱葱的桑树是如何茂盛、桑树枝上红得发紫的桑果是如何好吃……我一口答应了。年轻人做事干脆利落,说走就走,正好第二天就是星期六,这样第二天上午,几位山里的同学加上我及家在西塘的同学来到火车站,买票上车了。一个半小时后,火车就停在了嘉善县城的老火车站,下了火车,出了车站,朝南步行到汽车站,坐上了开往窑廊(即干窑)的汽车。约半个小时,汽车就到了窑廊,然后一行人由我领路穿过窑廊的老街步行了一个小时到了我家。到我家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
因为我们是突然到家的,父母亲事先不知道,那时可不像现在只要手指一点,信息立马就到,所以我父母显得有点忙乱,甚至有点手足无措:一是家里房子不宽敞,一下子多了四五个人,晚上睡觉怎么办?二是来了客人总得招待吧,在偏远的乡下,一时三刻到哪里去买菜。好在大家都是同学,又都来自农村,农村的情况当时都差不多。大家都无所谓,只是图个开心。
我妹妹在我读师范期间到过一次学校,跟我的同学见过面,算得上认识,所以大家也就少了拘束,少了陌生,多了随和,多了亲切。
买肉是来不及了,好在家里养着鸡,就只好委屈它们了。我家住在红旗塘边上,红旗塘南岸正好有渔民捕鱼的簖(拦河插在河里的竹栅栏,用来阻挡鱼、虾、螃蟹,便于捕捉),就在我家东北角。父亲说下午这个时候他们那里应该有鱼卖的。二话不说,一帮同学就跟着我直奔那张簖处去买鱼了。他们倒不是要看我怎么买鱼,其实是为了看看簖,因为山里的小溪里是见不到簖的。运气也真好,那天簖里正好鱼多,我们赶到时鱼还没卖完。我们就买了两条很大的花鲢鱼回家了。那时红旗塘簖里主要是白鲢、花鲢之类的鱼居多。
等我们拎着鲢鱼回到家时,母亲和妹妹已将鸡杀好了,正下锅煮呢,白斩鸡是一道比较简单却又拿得出手的农家菜。我们便开始七手八脚地杀鱼。而后,我们自己动手,烧火的烧火,上灶的上灶。不一会儿,鸡呀,鱼呀,炒蛋呀,青菜呀,毛豆呀,都上桌了。虽说厨艺不高,但因为是自己做的,大家都很开心。
大家边吃边喝边说着大话,记得当时有同学还来了个即席赋诗,诗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说张簖的红旗塘及我家后面的那条小河的水如何好之类的。在当时,这样宽阔的大河,这样清澈的小河,对生活在山里面的同学来说当然是羡慕得不得了。其实他们那里是有山有河还有海呢,只不过我这几位同学的家正好在山里头,离他们那里的大河或者海都很远。吃罢晚饭,趁着黄昏时的亮光,我又带着这些同学到了红旗塘的桑树地里,去寻找那些还残留在桑树枝上的桑果。晚上,六七个人挤在两张竹榻铺上天南海北地嗨聊到深夜。第二天吃罢早饭,又步行到西塘同学的家里,大家想去看看他家旁边的祥符荡(这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表)。
老屋后的这条小河存在的时间不算长,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又被填平了,不过在填平之前,在地下埋了很粗的水泥管,作为公场周边农田的放水暗沟,仍连通外边的浜。因为后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来分开的两个生产队又合并为一个生产队了,再后来分田到户,原来分开的八队的仓库、公场等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小河填平后被平整成了菜地,分给了好几户人家,我大哥二哥也分到了一点,我父母则在原河桥头处种上几棵梨树,但终究因为地处屋后,阳光不太充足,光开花不结果。后来大姨家也由外浜口搬到了我家的东面,与我大哥家为邻。表姐家就在原小河河底头的地上种上了竹子,后来变成了一片不大不小的竹园。
如今再回到乡下老家,原先老屋后面的小河早已无迹可寻,浜里的年轻一代如果不跟他们讲起,他们是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一条小河的,但临浜的水泥路旁那间抽水机泵房还可证明这里原先有过一条小河。
尽管老屋后的小河生命是短暂的,但它见证过农村发展史上的一个片段,并且曾经带给我们方便,也给过我们欢乐,我们还是应该记住它曾经的存在。
老屋后的小河一直在我梦里流淌着,无论走到哪里都时常想起它的模样,那是家乡的记忆,那是美丽的乡愁。这条曾经清澈的小河,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